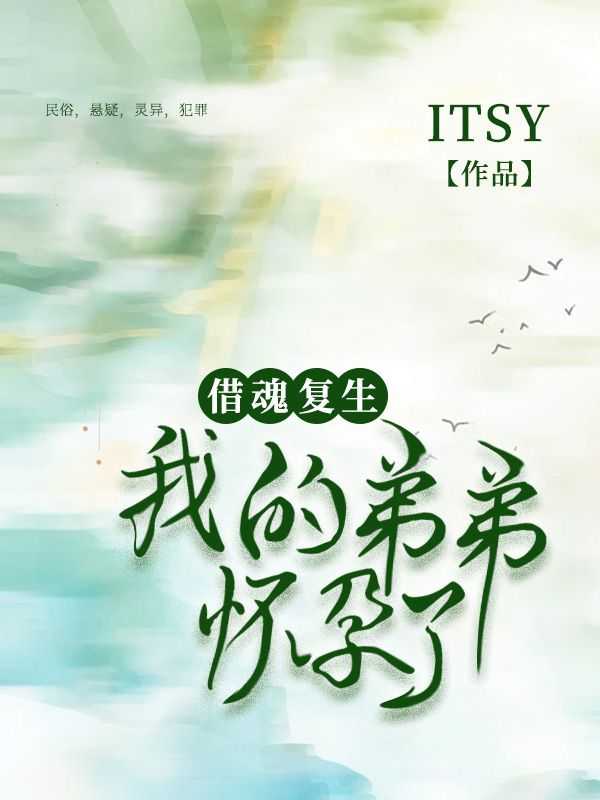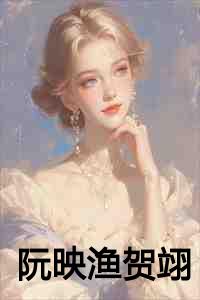元夕夜。 上京城,裴宰相府 屋外白雪皑皑,桌上的烛花即将燃尽。 秦倾颜抱着冷透的手炉,望着黑漆漆的窗沿。 一盏灯笼晃晃悠悠闯入。...![]()
元夕夜。
上京城,裴宰相府
屋外白雪皑皑,桌上的烛花即将燃尽。
秦倾颜抱着冷透的手炉,望着黑漆漆的窗沿。
一盏灯笼晃晃悠悠闯入。
“怎么还未安寝?”
裴攸尘推门而入,带起一阵刺骨寒意。
他看着毫无生气的秦倾颜,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“你身体不好,我不是说了让你不必等我。”
秦倾颜听着他一如既往冷硬的嗓音,娴熟起身上前替他更衣:“我忘了,以后不会了。”
秦倾颜低着头,外袍的寒意简直要钻进骨髓里。
裴攸尘最厌恶她这副逆来顺受的模样。
成亲七载,她好像永远都没有脾气。
当初若非皇上赐婚,他又怎会娶这样无趣的女人。
秦倾颜自知不讨他欢心,只默默整理着沉重的外袍。
外袍上沾染着淡淡的脂粉气,很是好闻,却几乎叫她落下泪来。
成亲那日裴攸尘嫌恶的让她少涂脂抹粉,呛得慌。因此成亲七载,她从未用过脂粉。
“怎么了?”裴攸尘见她停下动作,不耐蹙眉。
“没什么,夫君早些安寝吧。”
秦倾颜忍住鼻头的酸涩,若无其事的将沉重的外袍挂回衣橱。
她望向衣橱角落不起眼的包裹。泛白发黄的布料与贵气的宰相府格格不入,却是她唯一的行装。
今年,是她陪裴攸尘最后一个元夕夜了……
裴攸尘最不喜秦倾颜这副唯唯诺诺的模样,好像从进门那日,就再没变过。
她是整个京城盛赞的宰相夫人,却与自己貌合神离共度七载。
走到洗漱的铜盆旁,裴攸尘瞥了一眼旁侧冷透的药盅。
“不是说了我不喝参汤吗?”
秦倾颜闻言,心头一凉,她又忘了喝今日的药。
“抱歉……”
说着,她赶忙去收拾药盅。
可得到的却是裴攸尘重重的关门声:“我去书房睡。”
他好像回来了,又好像从来未曾来过。
凄冷的冬夜,秦倾颜独自缩在床脚,将那盅冷药一口口酌尽。
又冷又苦,宛如她嫁入宰相府后,整整七载的日子般难挨。
放下冰的刺骨的药盅,秦倾颜从怀里掏出一张叠的整整齐齐的信封。
拆开信封,“和离书”三个字在晦暗的烛火下摇摇欲坠。
裴攸尘不喜欢她,她早就知道。
成亲以来,裴攸尘不是宿在书房,就是彻夜不回。
紧了紧披在身上的锦被,秦倾颜细想成亲这七载,真如“日暖月寒,来煎人寿。”
第二日一大早。
秦倾颜天还没亮就起床安排宰相府的各色事务。
而裴攸尘则匆匆吃过早饭,准备上早朝。
他总是如此忙碌。
秦倾颜想起自己刚嫁进来时,什么事情都手忙脚乱,经常一整夜一整夜的对着府里的账本对账。
裴攸尘从不曾想过,为什么府里大小事务都井井有条,为什么大家都夸耀相府家风极好。
“下完朝,去正厅拜见父亲母亲。”
裴攸尘说完,站起身,只等着秦倾颜为她整理衣襟。
秦倾颜放下刚咽了一口的白粥,细致的替他理好衣裳,心中却含了满腔酸涩。
裴攸尘拜见的,是他的父亲母亲,不是自己的。
她一时如鲠在喉,片刻,从袖里掏出一封叠的整整齐齐的信封,递交给满脸狐疑的裴攸尘。
“大人,我们和离吧。”